最近正好在读去年从北京买回来的《李瑞环谈京剧艺术》,而李瑞环同志近来恰好又搞了一个手制家具展。趁着这个当口,聊点儿读书和读书以外对于李同志的印象,主要是京剧方面的。

《李瑞环谈京剧艺术》
现在只要在京剧领域里提到李大爷,首先能够让人想到的就是那赫赫煌煌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工程。“音配像”的手段虽非李大爷独创,但是把四百余出老录音利二十余年时间系统地配像并最终出版流传,实在是李大爷的头功。当然,音配像还是有一些众所周知的问题,如版本选择尚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等,可瑕不掩瑜,其功还是远胜于失的(在这里若用“过”就言重了)。即便若是今天某个大领导出来说我们来搞一套京剧音配像,都会因时非其时人非其人而难成其功。
不过记得在九几年中央电视台三套开始放音配像的时候,作为观众的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李瑞环的创意。《中国电视报》上的介绍也没有提及李瑞环的名字。后来音配像的片头开始放张君秋的一段谈话,提及了李瑞环。再往后出版的光盘盒子上,其介绍的第一句是“《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是李瑞环同志创意策划的”。这个工程才与李瑞环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
音配像之后,李瑞环又搞了一个“像音像”。这个玩意儿小豆子没看过,不过看了介绍觉得实在是一个无聊的鸡肋工程。按照李大爷自己的说法,这个东西是这么搞的:“首先在剧场演出取像,力求最好剧场效果”——这样做是因为演员在剧场演出有激情有气氛;“然后在录音室看录像录音,看像只是为了解决大体尺寸问题,不对口形,放开唱,以求最佳声音效果”——这样做是录音效果好;“最后再搞音配像,自己给自己的音配像”——这样就有了高质量的音和像。
李大爷在他的书里不止一次提过他是搞建筑的,所以对于很多细节上的瑕疵都无法容忍,力图尽善尽美。比如若是舞台上的桌椅没有摆正,他看了都会很难受。这一点可以理解。但对于追求一出戏的录音录像效果到了上面所见的地步,就实在让人乍舌。其实,以现在录音录像手段之高,完全可以直接从剧场采集演出实况,经过多机位剪辑来制作出音像都是上乘的作品。若担心剧场演出中可能会有差错,则可直接在电视台里静场录像。有无激情气氛,并非一定要靠底下观众来烘托的。况且,在眼下这个时代,老艺人一个一个离我们而去,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地把濒临失传的剧目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保留下来,或者把已有的老录音老录像修复整理出版,而不是在音、像、音这种细节上无休止地要求完美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很多人觉得李大爷是懂戏的。而读罢他的这本谈京剧艺术的书,给人的感觉却是他并非真懂。其实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他若是完全不懂,那就可以直接指派一些内行来负责,自己不去干预(就如同音配像工程那样);而他若是完全懂行,则不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唯有这半瓶晃荡的情况,又要对一些剧目做指导,又指导的不是地方,才是最可怕的。
比如李大爷说《四郎探母》,认为不应该上四夫人,盖有损杨四郎作为主角的光辉形象。这就是十足的乱指挥了——砍掉了“你苦苦地拉我为何来”那夫妻暂聚即分的伤情,而去按样板戏那样去塑造主角的高大全。作为一个领导,当他提出来对杨四郎的原配夫人有意见时,那还了得,四夫人就只能待在汴梁不随军“征北塞”了。
比如李大爷改编的那些剧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喜欢京剧,但谈不上内行;我重视剧本,但改编剧本不是专长”。李大爷虽然有自知之明,却仍然连动了《楚宫恨》、《西厢记》、《金山寺·断桥·雷峰塔》、《生死恨》、《刘兰芝》五出戏。领导亲手操刀,院团哪有不演之理!试看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委常委蔡赴朝,鼓捣出一出《赤壁》来,都能让国家大剧院倾力排演,何况李瑞环同志。当然,李大爷这些改编剧目的搬演都已是他不在任时候的事情了,相比那些在势之人动用权力而满足一己之私欲,已是强得很多。但作为老同志,又是老常委,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能不在自己不熟的领域插上一脚,还是不插为是。
虽说李大爷只是半瓶子,但从他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真心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真心喜欢京剧这门艺术,真心想为京剧做点儿什么的。不过这种事情,往好了说,是于京剧有利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以说是“以权谋私”,纯属灰色地带。举书中所见的几个例子:
比如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去北京演出,李瑞环说:“演出时,我们准备给你们张罗一点人去。几大坨子,铁道部以吕正操为首,有几个京戏迷,现在就往这里打电话;体委荣高棠、李梦华;还有海关总署署长戴杰和两个副署长,京戏迷。”
比如关于青年团1987年的财政,李瑞环说:“今年你们财政的开支大体是这样的,你文化局那个钱,该给的还给,市里再给你们补助二十五万吧,来源是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葛子平给十万。我跟他说给青年团十万吧,大年三十,你给我拜年嘛,给十万块钱。昨天我跟白化岭说,他哭穷,说今年天津压了五个亿,压得很苦,没钱怎么办?我说你再给十五万。”
比如“百日集训”时把张君秋从北京请来,李瑞环说:“君秋同志的影响比较大,能把他搬出来这么长时间,圈在深宫大院里不准出去,很不容易。你们可能也受点气,他不高兴就发火了,他那火也不完全冲你们来的,把老头儿往那儿一圈,走吧,不好意思,不走,圈着又真难受……张君秋怎么可以在这儿憋一百多天,我看在他这一生里头是不会有的。山东不是请他吗?贵州不是也请他吗?他说:我这一辈子,谁请我到哪儿待个十天八天顺便说说戏可以,再像天津这样是没门儿啦……不是老谢讲嘛,你们那个市长调动积极性还真有本事,把张君秋调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去年是为了张君秋在天津住一百天,就把刘少奇原来住的那套房子拿来给他住。一所花了十万块,我向毛昌五要了五万块。君秋那房子一天三百块钱。”
比如关于孟广禄拜山东的方荣翔,李瑞环说:“孟广禄和方荣翔,我是搞了个交换。我一听可以,我说给方荣翔,我找到省长,省长说,我交响乐在天津演出的时候,你得去给我捧场,给我组织观众,要不然我不收,那天我拉着倪志福都去看了交响乐。第二天,我跟天津日报的人说,要吹一下。李省长夜里打电话说,这个徒弟收了!”
以上这些内容,并非李大爷在什么正式场合的讲话内容(正式场合的讲稿一般都很空洞很官方),而是在与青年团的演员谈话时脱稿的讲话内容;并非什么秘闻,而是正式出版物上的摘录。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即李大爷并不认为这些走关系捧场要钱找师父一类的事儿有什么不妥,而作为国家领导人,或者说当时作为直辖市的领导,李大爷的纪律性还是差了些。这对于我们戏迷来说,他是办了好事儿,可如果他用同样的行政权力去做其他一些“谋私”的坏事情,这又当如何?好事与坏事又如何界定?从法治的角度来讲,“违法乱纪”的性质不会因所做事情的性质的不同而不同,那这样的事还是不做为妙。
顺便推荐一下这本书吧。之前说了,在大面儿上讲的那些话没什么内容,都是写好的官方发言稿。私下与演员们的交谈,有很多内容。你可以理解李大爷“百日集训”的目的;你可以看到李大爷对于青年团所寄予的厚望;你可以了解李大爷的艺术观与历史观;你甚至可以明白被李大爷看好的刘桂娟为什么现在能够发展去当“公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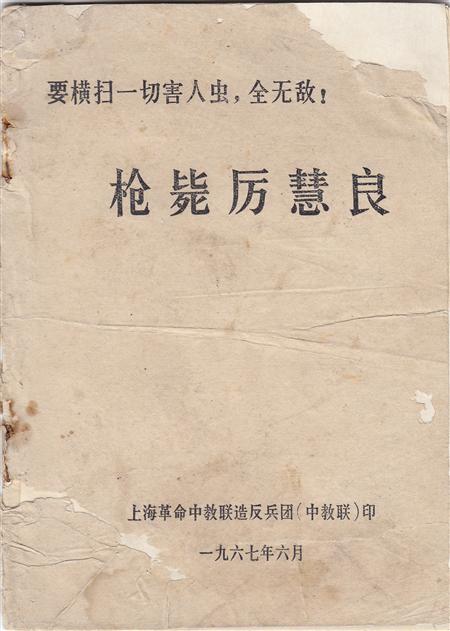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