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整理《风尘三侠》的本子,里面的词句雅得很,一些定场诗和引子都很不错,也做了摘抄。后来一查,原来里面的词句很多都是直接搬自《红拂记》传奇,这也就难怪了,雅得不太像乱弹。
于是想起来《红拂传》这出戏,翻出了多年前买的王吟秋和赵世璞的DVD来看。这一版从中段开始,没有红拂夜奔的内容。
吴小如先生在《吴小如讲杜诗》一书中曾经提过他八十年代看王吟秋的演出,最后一场李靖、红拂与虬髯公饯别,红拂南梆子唱罢舞剑,舞剑之后应有最后一句“此一去再相逢不知何年”,那场王吟秋舞罢就没有唱。吴先生后来把他的想法告诉了王吟秋,王吟秋之后补录了那句。但是显然王先生后来再演也还会省掉这句,这版九十年代的录像即是明证。大约随着年龄的增长,舞剑之后需要喘息,无法平静地把最后一句唱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只不过就没有做到真正的“豹尾”。关于这段的原委,摘抄一下吴先生的文字:
我是戏迷,戏的结尾不容易结好,我看过程砚秋的《红拂传》好多次,程演《红拂传》有个条件,必须是侯喜瑞唱虬髯公。20世纪50年代初,程在天津唱,正赶上侯喜瑞在,我一看马上去搞票,要看这出戏。我主要想看侯喜瑞,程当然也好。程当年拿这戏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较劲,《霸王别姬》是1921年开始排演,1922年正式演出,靠舞剑叫座。程此戏,红拂与虬髯公分手时也舞剑,《别姬》唱二六,这个唱南梆子。我看过好几次,舞完剑戏就完了,这一次我坐得很近,舞完再唱一句。插一句,梅兰芳晚年演《霸王别姬》,舞完最后一句不唱了,那一句是“宽心且把宝帐坐”,再下一句“待听军情报如何”唱不唱无所谓,晚年就不唱了,这一句省略了没关系,不影响剧情。可是程《红拂传》的最后一句是“此一去再相逢不知何年”,这句不能省。最后唱这一句,我哭了,真是感动。剧情是一个饮酒的欢娱场面,舞剑助兴,舞完了,就是这一句,红拂内心的话说出来了。这不就是杜诗的“世事两茫茫”吗?这是50年代初的事,1958年初程先生故去。到了80年代,程的徒弟王吟秋也唱《红拂传》,他给我送了一张票,在民族文化宫,舞剑之后,王也把最后一句省了,我觉得很遗憾。他没有体会那一句真正的分量。第二天一早他来看我,征求意见,我就把自己的感受跟他说了,我说最后一句不能省,要唱出最深的感情。王很虚心,后来他在中央电视台录像,把这一句补上了。过去人讲做文章要“凤头”、“猪肚”、“豹尾”,这个“豹尾”很重要,杜甫“明日”两句,就是“豹尾”。这两句思想感情,与程砚秋的戏最后一句一样,越琢磨越深。
这是看录像时见到的“减法”。另外,在剧中,徐洪客和李世民对弈,试看李世民之手段,一旁虬髯公和李靖观棋。这里赵世璞搞了个“加法”,添了一段莫名的二六,其中有“双车直入夺魁首,骏马奔驰炮当头”之语。固然戏里面没有具体交代下的是什么棋,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两位国手显然下的是围棋,因为只有在围棋里,高手不必等到终局便可判定这里面的势,看出棋力孰弱孰强。加之下围棋比下象棋更要求人的全局观,也更雅致,符合李世民的“人设”。试想李世民和徐洪客俩人在那儿轮番“当头炮”、“把马跳”、“拱卒”、“将军”,弄得就像街边树下穿背心的大爷似的,烟火气倒也十足,可就没了世外高人的仙气儿。此处李靖只要像剧本里那样静观棋盘上风云变幻,转眼徐洪客推枰认负即可,不需要来这么一段多馀的唱。
这个录像所见的一加一减,都造成了对塑造人物和烘托氛围的破坏,实应该再多推敲推敲。当然,这种小处的改动相比现在的新编造魔,破坏性已经算是微乎其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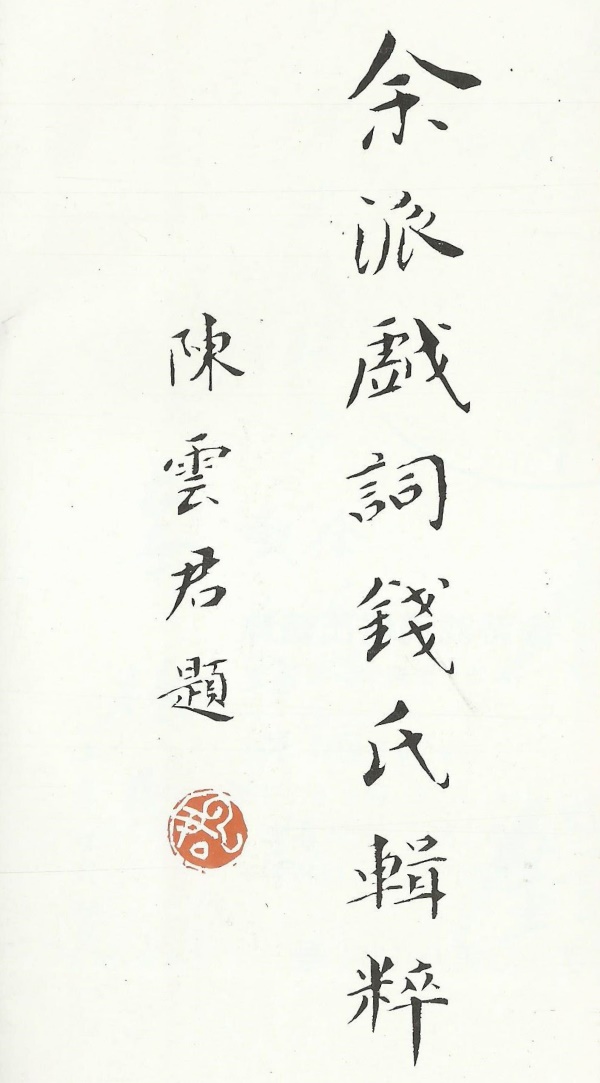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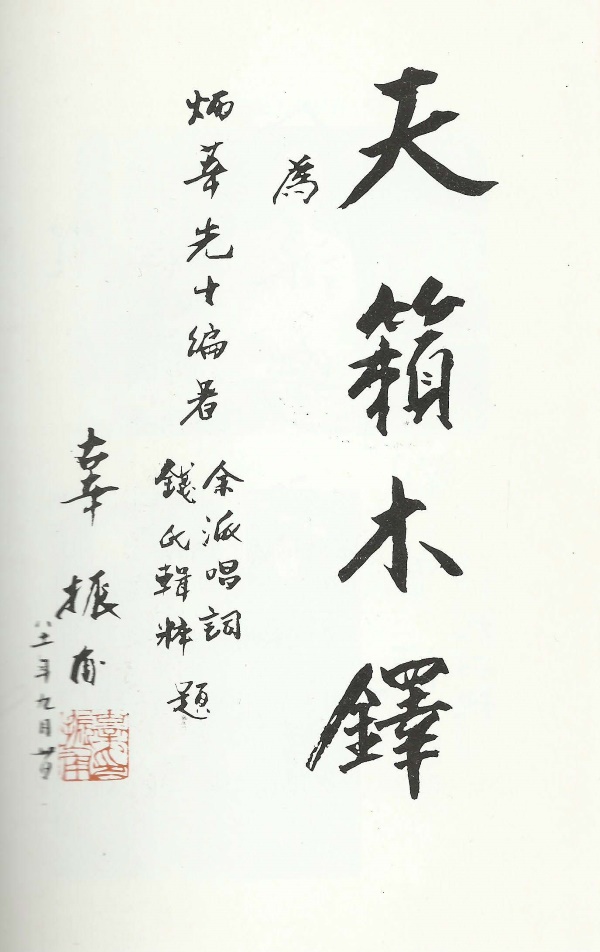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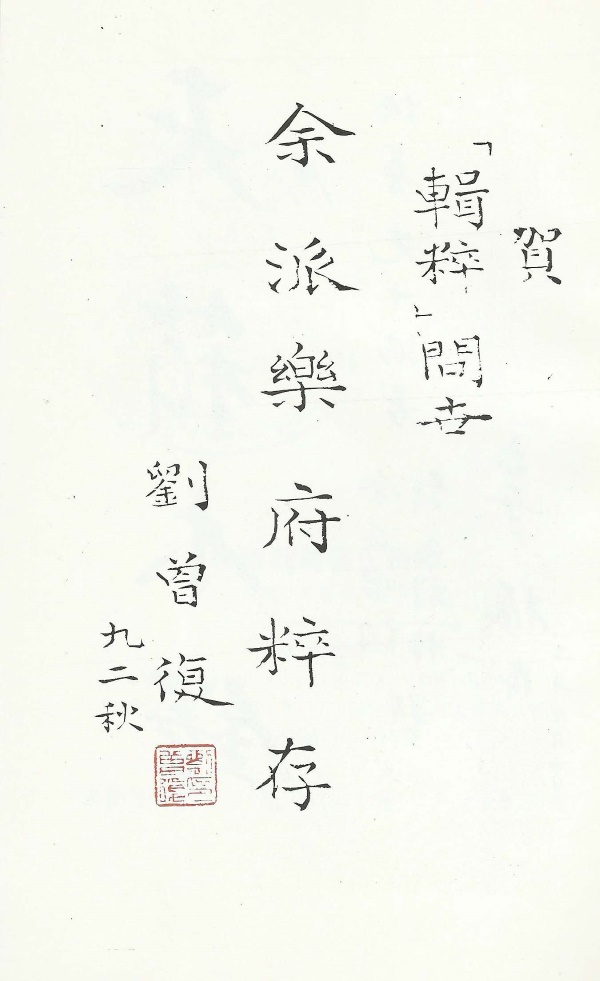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