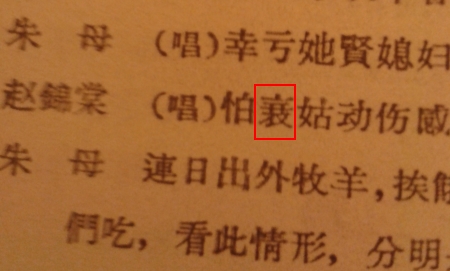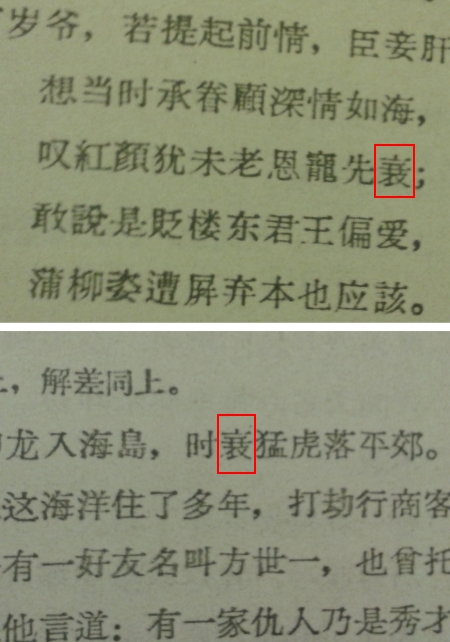读张恨水的杂文,看到一篇讲《打渔杀家》谬误的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以前没有注意过的细节:
《打渔杀家》,尚有一事,万万须改者,则为萧恩唱“夜晚”一段之后,桂英唱两句摇板。词云:“遭不幸我的母早已亡故,撇下我到如今一双大足”。将嫌大脚入于唱词,实属不雅……唱后接萧恩云:“为父叫你不要渔家打扮,为何偏偏渔家打扮?”桂英云:“孩儿生在渔家,长在渔船,不叫孩儿渔家打扮,怎样打扮(自然有理)?”萧恩云:“哽!不听父言,就为不孝(这叫无理取闹)。”桂英云:“爹爹不必生气,孩儿改过就是。”萧恩云:“这便才是。”不知为何要加入此一段。殆编剧者甚恨大脚借题发挥欤?
把《戏考》翻出来看了一下。这个本子整理得比较早,已经不记得了。原来以前演这戏的时候,还真是类似的唱词:
遭不幸我的母早年亡故,
抛下我到如今一双大脚。
这里的“脚”显然是按照上口字 Jio 的发音走的,和萧恩前后的唱一样,都是波梭辙。
萧恩父女二人后面的对白,在现今的舞台上并没有改动,这大约是前辈艺人对这段对话有自己的理解。比如读周信芳的文章,可知他认为这段对话,是第一场戏和第二场戏之间暗场交代的故事:因桂英出嫁的日子越来越近,所以萧恩便让桂英不再渔家打扮,同时觉得女儿就要出嫁,自己便无牵无挂,不受作渔家的气了,一边欢喜,一边又不舍女儿,因此“昨夜晚吃酒醉“。而桂英则是对于自己的婚事害羞,没有立刻改装,因此上场之后也是有犹豫的神态。这段对话没有了前面的“大足”,也就没有了无理取闹之感,保留着倒也无妨。
倒是桂英自叹的“大足”唱段,如张恨水所愿,早已随着缠足本身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看民国后期的剧本便已经是这样了,更不要说已经留下来的录音和电影,也都不见了“大足”之叹。原编剧者在剧中为何突然让萧桂英对自己的“大足”大发感慨,不得而知。这个插入非常突兀,难怪张先生会觉得编剧“甚恨大脚”。
作为劳动妇女,萧桂英本不应该为自己的大足叹息,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剧中的古人与今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境界。而且即便今天的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束缚,却仍然会面对其他泛起的旧道德沉渣,各式各样的“天花板”,甚至包括加于身上的有形锁链。男女平等,前路依然漫长。
国际劳动妇女节前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