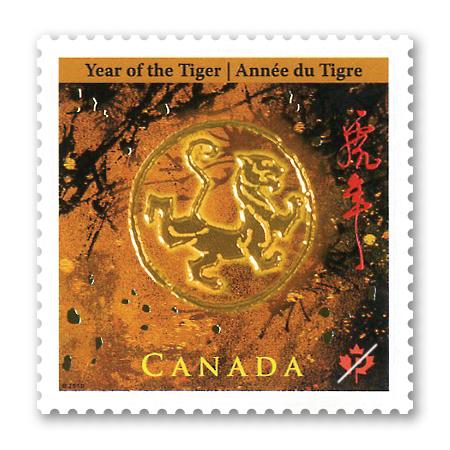《武昭关》这个戏,时不时拿出来听听,很有意思。
这戏不仅是好听了,生旦对儿戏按说一大把一大把的,但现在舞台上演来也就是《武家坡》、《坐宫》什么的。稍微复杂点儿的《汾河湾》,大约因为没有好的娃娃生,来不了了;再比如《桑园会》,老旦可能也没人给配,也不来了。不过像《武昭关》这样的戏,其实倒是可以在舞台上常演演,比如那些唱惯了《文昭关》的“当家老生”们,可以带着常傍着自己的青衣来出《武昭关》,反正这也是大陆戏,无所谓流派,时间上也不算长。
说起《武昭关》,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一出引入了“平行世界”这种概念的艺术作品吧。
京剧里,《文昭关》和《武昭关》是所谓“并存”的,即两出戏都是讲伍子胥走国逃出昭关,但是所经历的事情完全不同。《文昭关》里的伍子胥碰到了隐士东皋公(一会儿再说他),在花园里躲了七天,一夜白须,这才混出昭关。而《武昭关》里则是伍子胥保着马昭仪母子俩逃走,困在禅宇寺,直到马昭仪投井,伍子胥才抱着小太子突围。科学地说,伍家被害伍子胥逃出樊城之后,伍子胥的世界就分裂了,产生了两个平行世界:伍子胥在一个世界里碰到了东皋公,以“文”的方法过关;而另一个世界里的伍子胥扎着靠大战,也换了三次髯口,“武”了一场才算过关。
除了《文昭关》、《武昭关》以外,京剧里《四郎探母》与八本《雁门关》的关系,也是平行世界里发生的,互不相干。
《姚期》和《打金砖》也是这样。记得以前第一次看《打金砖》,那会儿已经看过《姚期》了,所以自认为对故事情节比较了解,主要就是来欣赏不同的演绎方式了。结果当马武请了赦旨转身要出宫救姚期的时候,大太监端着人头就上来了。当时看得小豆子一惊,心想这姚期不是在另一出戏里给保下来了吗,怎么到这儿就没救成了?后来再看刘秀在太庙里的表现,才知道这出戏把姚期给砍了就是为了刘秀的表演。再以后看《汉宫惊魂》,那姚期的世界已经不止分裂成两个,而是三个平行世界了。
为什么我们一段历史故事可以分裂成好几个不同的情节和结局?这大概和我们的历史观有关系。我们对于历史故事有着极大的再创作自由度,以至于现在看来很潮的“平行世界”啦、“穿越”啦等等概念,在我们的历史演义中比比皆是。
再比如上面提到的《文昭关》中的东皋公,自称“曾拜扁鹊先生门下为徒”,而这位战国时期著名医生的徒弟竟然穿越回到春秋时代,大约这位“时空旅行者”的任务也就是来专门搭救伍子胥的吧?

 否则是无从知道理发店里有长龙存在的。
否则是无从知道理发店里有长龙存在的。


 另外对不住合意太爷,这次没空儿聚了。
另外对不住合意太爷,这次没空儿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