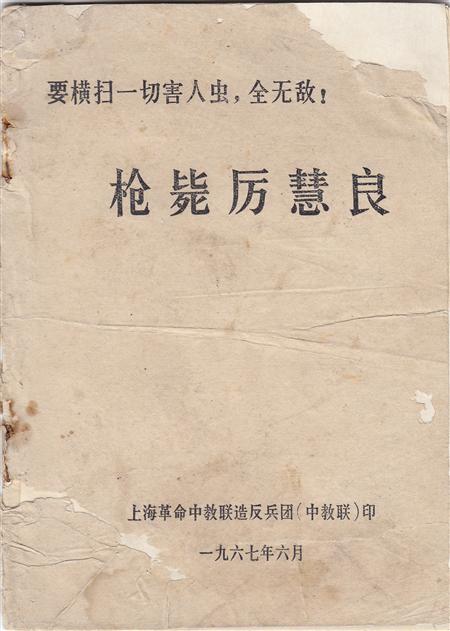七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阿联酋,出差。趁着现在还记得一些,并且没有前几天那么忙了,写下点儿什么。毕竟,这种地方不是说去就去的。
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说阿联酋这个国家,应该是某次足球比赛,咱们的国足和他们踢来着。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亚洲有个名字听起来像球一样的国家。说到足球,阿联酋本地的媒体竟然还会关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无论报纸上还是电视上,体育新闻板块都会有所覆盖。也许,有些东西从远远的地方眺望比离近了瞅要好看吧。
在去阿联酋之前,做了一些功课。这个神秘的地方,传说是极具阿拉伯保守风格的。比如,男女不能当街拉手(当然,作为和同事出差的小豆子不用担心会犯错误),女同胞不要穿着暴露,等等。
到机场之后,排队过海关。放眼一望,海关的官员都是白色的长袍,包头巾、头箍、拖鞋,传统的服饰。看来,尽管西方的文化在冲击着世界上各个角落,在中东这一隅,阿拉伯传统服装还是相当有市场的。
事实上,阿联酋并不是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西方文化的冲击还是随处可见。在迪拜的各种大型商场里,满眼都是写着洋文的外国专卖店,如果不是走在商场里随处可见的长袍男和黑袍女,你甚至不会意识到这是在阿联酋。这些漫步的人,除了身着传统服装的本地人,还有一大半穿着各种服装的本地人和外地游客。之前做的功课基本上都没用了:你可以看到短衣短裤的妇女,也可以看到牵手的情侣,甚至于,在一个英国风格的酒吧里,你能看到真主安拉的追随者抓着酒瓶豪饮。这是一个各种文化信仰交融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和我朝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他们个体身上所带的传统符号,更加明显,因此,这种不同文化特征的同时出现显得更加“耀眼”。

迪拜现代化商场中的各色游人
看来,任何文字上的描述都不能准确并完全概括一个地方文化的状态,而固然几天的行程亦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深入其中的体验,还是比流于文字表面要好得多。
不得不又说回我们的传统艺术。如今,对传统艺术有兴趣的新一代越来越少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多少亲身接触这些文化和艺术的机会了。想了解京戏,自然要走进剧场去看,通过广播去听,耳濡目染,熏陶。诚然,现在的社会环境是多元的,不似以前那样只有几种艺术形式。但也正因为此,国家也好,电视台电台也好,既然喊出了要继承振兴的口号,那就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大众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艺术,就像一个旅游地希望游客体验当地的文化,就会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游客来访那样。我们不是也有时候指责一些连中国都没去过的外国政客如何对中国的情况指手画脚么?
当一场戏的票价动辄上百,当广播里很难听到戏曲的声音,人们对这些传统艺术的认知也就只能停留在旁人的议论或者文字的描述上了。而这种停留在非亲身接触的认知,对了解一种文化艺术毫无帮助,只会产生各种的偏见。像到达阿联酋之前听说的封闭保守的文化那样,没有条件接触京剧的人会继续以为这个艺术形式节奏慢、唱腔拖拉,甚至是所谓的只有老年人才喜爱的艺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周末大戏台”节目,节目开头是这么说的:
不进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不进周末大戏台,又怎能知道这戏苑百家,精英荟萃!周周有好戏,周周都精彩,欢迎走进周末大戏台!
“走进来“的道理显而易见。不过,中央台把这档戏曲节目放在“老年频道”播放,而且多少年如一日地在这档周末节目里重复播放梅兰芳、马连良的《汾河湾》、裘盛戎的《牧虎关》、王玉磬的《辕门斩子》等不出十出戏的录音,来来回回地播。这种作风和暗示,又能让多少路人通过这个戏台“走进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