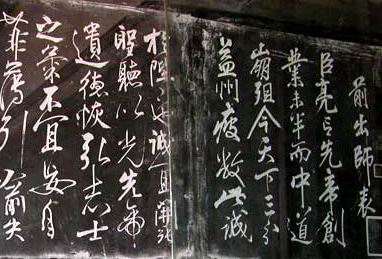南北两大京剧院头头儿发话了,摘录部分,来“批判”一下:
① 本报记者近日特约两大京剧院院长——北京京剧院副院长周铁林和上海京剧院院长孙重亮作独家专访,在访谈中他们一致指出戏曲的希望在于“变”:“因为对于今天的戏曲来说,‘守’城是根本‘守’不住的。”
② “京剧原先就是‘袍带戏’,它的表现形式比较大气,所以也适合说一些帝王将相的故事。可是今天的京剧要赢得观众,再演那些传统的‘袍带戏’已经不行了,得创新。”孙重亮说。上海京剧院的《狸猫换太子》,题材其实早在元朝就有了,算是标准的“老汤”,可创作者却巧妙地换了“新药”。“重点没放在那些帝王将相上,而是三个小人物——一个宫女,两个太监,着力挖掘普通人的情感。”结果,这个早在新文化运动时便被戏曲界判了“死刑”的剧目在20世纪末又复活了。
③ 北京京剧院的《袁崇焕》,主人公是明末名将袁崇焕。似乎仍是“袍带戏”,其实内容却是大不同——老式的袍带戏大多宣扬皇权思想,但《袁崇焕》说的却是爱国精神。“如今都说要继承传统戏曲,但其实继承只是第一步。戏曲要往前走得更远,就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升自身承载的内容。”周铁林说。
④ 《狸猫换太子》之所以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被判“死刑”——当时的人们这样批判它:“京剧发展到《狸猫换太子》的地步,也算是腐朽衰败了。”——那是因为经历了元明清数代后,该剧竟长达25本,其中不仅充满了各种封建糟粕,而且情节东拉西扯,惹人生厌。于是,上海京剧院在决定“拯救”这个传统剧目后,头一个制定的原则就是情节绝不能拖沓。后来问世的《狸猫换太子》总共有三本——期间总共花了四年时间打造,而这次人们在佛山见到的索性只有两本。“我们之所以决定‘缩水’,是因为现在的观众跟十年前又不一样了。改短一点,更能符合他们的心理节奏和生活习惯。”孙重亮说。他承认,戏曲的这个做法是源于电视剧的启发,“你瞧,现在的电视剧究竟是节奏快的受欢迎还是节奏慢的受欢迎?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
⑤ 周铁林说,《袁崇焕》在节奏上的思路跟《狸猫换太子》的相同。“虽然故事是以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基础,可是在编剧的精心安排下,观众只需要一晚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看完。”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节约空间”,全剧在结尾处索性打上了“字幕”,简单而又意味深长地交代了袁崇焕被凌迟后又被乾隆翻案的结局,这个做法也是从电视剧和电影中学来的。
就凭这五点,两位院长可以下课了,因为他们连京剧怎么回事儿都没搞明白。
对于第五点,所谓京剧的节奏问题,竟然把电视剧搬出来说节奏快是和电视剧学的,还说“编剧的精心安排下,观众只需要一晚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看完。”笑话,请问有一集的电视剧吗?京剧的速度从来就是比电视剧要快无数倍,自来的“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还有比在台上转一圈万水千山过去了要快的吗?京剧需要字幕吗?所有暗场不都是可以通过演员自己交待出来的吗?京剧从来不需要和任何艺术学什么,就早已有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节约空间”、“节约时间”,甚至“节约开支”的问题了。
对于第四点,所谓连台本戏“东拉西扯”的问题。请先搞清楚为啥会排连台本戏,不就因为头本、二本吸引人,才越排越多。没错,里面是有东拉西扯、封建糟粕,但这绝不是像电视剧那样先定好了拍个25集电视剧,然后拍完放映。能排出25本来,正是说明其受欢迎的程度。请不要以“新文化运动”的眼光去看待曾经辉煌的连台本戏,也不要拿京剧和电视剧去比,更不要因为什么受欢迎就去迎合、去改变。
对于第三点,老式的袍带戏就是“大多数宣扬皇权思想”吗?传统戏里不光有《袁崇焕》所谓的爱国精神,而且还宣扬忠孝节烈、仁义道德。可笑的是,院长们还大言不惭地说“要继承传统戏曲”,你们继承了多少啊?
对于第二点,“京剧原先就是‘袍带戏’”。笑话,那么多才子佳人戏,那么多玩笑打闹戏,那么多平头老百姓的戏,这些京剧曾经演过的传统剧目,就被这“就是‘袍带戏’”给否了。既然否认袍带戏“不行了”,那请院长们恢复上演一下什么《打钢刀》、《打砂锅》、《打樱桃》、《打面缸》这样的小戏啊。实际上,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京剧院继承下来的传统京剧就剩下袍带戏了。
至于第一点,“守不住”了!大有“守不住来将我丢”的劲头。难怪京剧现在变成这样,原来领班的都是群大呼“守不住”而“反穿裙另嫁夫男”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