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008年央视春晚下载看完了。
点评今年的戏曲部分比较简单:因为头一段《对花枪》和末一段《四郎探母》竟然和两年前的春晚一样,太糊弄事儿了。我们的京剧唱段不是就那么少吧?仅仅隔了一届就又给搬出来了,而《对花枪》再次因应景改词儿,足见编导的目光短浅到何等地步。另外京剧的三段唱全是快板,像赶集一样完成任务,根本没有让观众去欣赏这个节目的意思。
京剧剧目之多之广,到如今虽然已经被糟蹋得不剩几个,但就算在这所剩无几的戏里挑些喜庆的唱段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而春晚的编导非要拧着干,先把《对花枪》的悲情词儿改了,然后又把《杨门女将》灵堂一场搬出来,却让个丧了亲夫的穆桂英穿大红。编导同志似乎有一种非要把悲情戏硬改成喜庆戏的癖好,其坚韧不拔的劲头着实令人吃惊,不惜以改词儿甚至穿错服装为代价,老话的“宁穿破不穿错”早不放在心上了。
春晚的京剧唱段不知从哪届起就是以快板为主,加几处翻高的地方,就算万事大吉。今年“叫小番”一段更是目的明确,仨孩子上来就唱三句,“叫小番”一完即刻打住,“扣连环”这种节奏稍微慢些的末句都没工夫唱了。如此发展下去,大约再过若干年,春晚的戏曲节目就一句“叫小番”完事儿。
倒是夹在京剧中间的豫剧和越剧节奏适度,让小豆子这样不懂豫剧、越剧的,都感到舒服耐听。三段京剧,太闹心了,你们着什么急呢?
有人说小豆子应该尽量避免找央视的茬儿,找茬儿在当前环境下不利于解封。但茬儿不是专门找的,谁让他们自己本身有那么多问题呢?
那么顺便说点儿好的吧:谢天谢地,今年的戏曲节目没有伴舞的了,虽然龙套也不少,但就站在后面,当个人墙而已,至少在视觉上不显得闹腾。
在不指望春晚能够完整上演一折戏的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说:我没招谁啊,别老拿我说事儿),就那么几个唱段还选不好,真是悲哀。悲哀的程度大约可以和豆妈看到灯罩版的章子怡相提并论吧——心目中的好玩艺儿,就这么给春晚糟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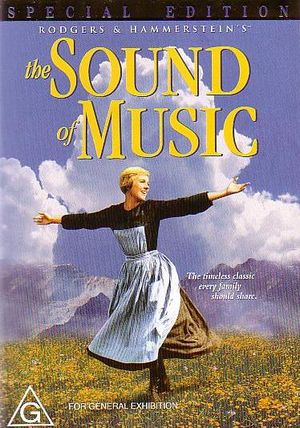


 。于是当时就推测出来了,这个版本的法海是花脸来的。其实心里更倾向老生来法海,主要对李世霖所录的那版录音印象很深,加上这戏正角是花衫加小生,没有个正经老生的角色。当然,花脸来法海也是大嗓,不过个人感觉是,花脸去的法海比老生去的法海要邪恶一些。而法海在小豆子心目中是没有那么邪恶的。理由?以后再谈了。
。于是当时就推测出来了,这个版本的法海是花脸来的。其实心里更倾向老生来法海,主要对李世霖所录的那版录音印象很深,加上这戏正角是花衫加小生,没有个正经老生的角色。当然,花脸来法海也是大嗓,不过个人感觉是,花脸去的法海比老生去的法海要邪恶一些。而法海在小豆子心目中是没有那么邪恶的。理由?以后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