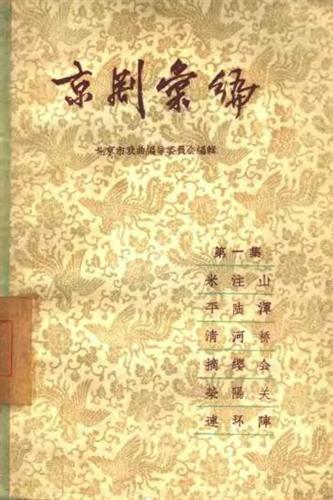《武家坡》徐东霞饰王宝钏、徐东明饰薛平贵
薛平贵在武家坡前的一场调戏,道德与否,人情怎样,暂且不论,单说就京戏而言,可谓经典中的经典了(尤其是在现在演员所会传统戏不多的情况下,更是被翻过来、调过去地演)。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薛平贵在窑前的大段唱的词儿改了:
(西皮导板)提起当年泪不于,
(西皮原板)夫妻们寒窑受尽了熬煎。
自从降了红鬃战,
唐王驾前去讨官。
官封我后军都督府,
你的父上殿把本参。
自从盘古
(西皮流水板)立地天,
哪有岳父把婿参?
西凉国,造了反,
薛平贵倒做了先行官。
两军阵前遇代战,
她把我擒下了马雕鞍。
多蒙老王赐恩典,
反将公主配良缘。
西凉的老王把驾晏,
众文武保我坐银安。
那—日驾坐银安殿,
宾鸿大雁口吐人言。
手执金弓银弹打,
打下了半幅血罗衫。
展开罗衫从头看,
才知道寒窑受苦的王宝钏。
不分昼夜往回赶,
为的是回家夫妻得团圆。
三姐不信从头算,
连去带来十八年。
那位说,小豆子啊,这段可不一直这么唱?不然,看一下老《戏考》:
(西皮导板)二月二日龙抬头,
(西皮原板)王三姐打扮彩楼前。
王孙公子有千万,
彩球单打薛平贵。
怀抱彩球相府转,
(西皮二六板)你父一见怒冲冠。
前门赶出薛平贵,
后门又赶王宝钏。
夫妻二人无投奔,
破瓦寒窑把身安。
楚江河下妖魔现,
红鬃烈马把人餐。
为丈夫擒了红鬃马,
唐王驾前讨封官。
封我殿前都督府,
你父一见把本参。
他说西凉造了反,
一封战表到长安。
唐王展开表文看,
吓坏了满朝的文武官。
苏龙、魏虎为元帅,
薛平贵倒作了先行官。
号炮三声崔前站,
平贵寒窑别宝钏。
王三姐难舍薛平贵,
平贵舍不得王宝钏。
马缰绳,剑砍断,
妻回寒窑夫奔西凉川。
三姐不信屈指算,
这连来带去有十八年。
不光老《戏考》,马连良、王玉蓉合灌的唱片中也是类似的唱法(大约因为唱片长度限制,精简了):
(西皮导板)二月二日龙发显,
(西皮原板)王三姐打扮彩楼前。
那王孙公子千千万,
彩球单打平贵男。
夫妻同把
(西皮流水板)相府转,
你的父一见怒冲冠。
西海岸,妖人显,
红鬃烈马把人餐。
为丈夫降了红鬃战,
你的父上殿把本参。
西凉国,造了反,
为丈夫倒做了先行的官。
校场以上把兵点,
平贵寒窑别宝钏。
王三姐舍不得薛平贵,
薛平贵怎舍得王宝钏。
马缰绳,剑砍短,
妻回寒窑夫奔西凉川。
三姐不信掐指算,
连去带来
(西皮散板)十八年。
三段唱,权且叫第一段为“流行唱法”,第二段、第三段为“老唱法”。这里的问题就是,哪种唱法要好一些呢?
首先,老唱法有其情感在里面,尤其是提到平贵别窑那部分,难舍难离,“马缰绳,剑砍短”,多少无奈尽在其中——一剑劈的哪里是缰绳,分明是十八年的光阴。流行唱法不但什么滋味都没有,而且让人一听:敢情要没那大雁骂薛平贵,这小子还不回来呢!虽然这也确是事实,但是很难想象,一个远途归来且已经弄明白自己妻子“贞节如何”的“当军的”,会对妻子说这种如同白开水的流水帐,而不是一些怀旧、温存的话语。
其次,薛平贵唱这一段,是因为王宝钏让这他位“当军的”说明白怎么回事情。那么对于王宝钏来说,十八年前窑前一别之后,薛平贵发生什么自然她是不知道了。按照流行唱法,你薛平贵和她讲什么又是“代战公主”、又是“坐银安”,有什么用呢?而像老唱法,把窑前告别这种只有他们两个人参与的前情“说的明白”,才能让当事人信服啊。
另外,按照流行唱法,在窑外面薛平贵提了与“公主配良缘”,王宝钏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进窑之后,薛平贵唱到“西凉有个代”突然停下来,王宝钏还那儿傻乎乎地说“带什么来了”,就显得不对了。同样的,在外面薛平贵已经说了“坐银安”,进来之后王宝钏还要因为薛平贵所说得天下而吃惊,也就不对了。而老唱法,没有提这些王宝钏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到后面再提就显得很顺畅了。
没有考证过《武家坡》和《汾河湾》产生的先后顺序,不过想来可能流行唱法多少借鉴了《汾河湾》里面叙述往事的手法,即叙述一些投军之后的事情。但,这些实在不是女主人公所能知道的,那她们有怎能凭这些去判断真伪呢?
不过流行唱法已经流行,且应该是在解放前就流行了。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去台的艺人也是如是唱,所以当不是因为大陆为破除封建迷信的吃人红毛儿马而单方面改动的。现如今凡是有唱京剧的地方,十有八九是有会唱《武家坡》的;会唱《武家坡》的,十有八九是按流行唱法去唱。老唱法,恐怕也就残留在老的媒介上了。